-
刘燕舞、魏程琳:一个乡村“精神病”的上访故事
关键字: 上访基层上访神经病人派出所警察涉警上访家庭纠纷朱的三个儿子均在市区买有房子,且生活相当优越,女儿远嫁在广东,但生活条件同样很好,孙子亦已成家立业,且也有很好的条件。因此,她判断,丈夫的钱既然不给她,又不可能给子女,就有可能给别人,这个别人最有可能是外面的女人。
这个判断让她抓狂。
最早的时候,朱发现家里的一个垃圾桶不见了,她怀疑是丈夫偷了给情妇。
于是,夫妻俩大吵,她丈夫觉得莫名其妙,并对她大打出手。结果是,夫妻分家,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生活。
但夫妻分家的结果更加让朱怀疑丈夫偷家里东西给别的女人,无论她丈夫如何解释,她都认为是狡辩,并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
朱让自己的生活作风更为“放荡”,但她以为是“秘密”,实际上,在邻近几个村都传为笑谈,她被远近村民讥讽为“每周一哥”,而这些“哥”们大多都是村里的老光棍,他们每次给朱支付数额不等的微薄费用。
2004年年初时,朱发现又丢了一个垃圾桶,她报警,并怀疑是她丈夫偷的。
后来,她又发现自己要做衣服的一块布不见了,这让她“千真万确”地“判定”是她丈夫偷了给了别的女人,她再次报警。
然而,警察不可能因为一个女人打电话报警说她丈夫偷了家里的垃圾桶或者一块布就出警,因为这在正常人听起来就觉得滑稽。可是,这在朱看来,她的垃圾桶和她的布是天大的事,她将自己等同于人民,认为人民的事,不管多小的事,人民警察就理应管管。
显然,朱对一个全能型政权乃至政党的期待,与现实无法完全吻合,这种张力,因为她的“神经”问题,而被放大到了极致。

公权力和普通民众都需要再教育
四、涉夫上访
因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朱的丈夫与她的儿子媳妇们对她都无法忍受,儿子媳妇们认为她给他们丢了脸,她丈夫最后搬到儿子那里住。
这一举动,让朱莉叶更加“坐实”了她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的“想象”,而且,她坚定了丈夫和子女都不管她的判断。因而,她开始找丈夫要“工资”,她说她早年含辛茹苦帮他生养四个子女,且承担了几乎所有家务和农活,现在老了,丈夫有退休工资了,理当应该管她。但朱的丈夫认为自己的钱要养儿子和孙子,这让朱觉得很搞笑。
一个要,一个不给。
于是,朱莉叶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她先给乡里派出所不断打电话报案,要求他们处理他丈夫,理由就是自己的东西被他丈夫偷了给别的女人了,这些东西,主要是垃圾桶,布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之类的。派出所开始还派警察下来察看,但通过从村民以及村干部那里了解,他们认为这个“神经病人”的话无法确信。
面对派出所的“消极态度”,朱开始到派出所上访。
派出所告诉她,上访要到乡里去找综治办。于是,朱便不断到综治办上访。
对于朱提出的很多啼笑皆非的诉求,综治办当然无法满足。
朱便开始找乡里的书记和乡长以及分管稳定的副乡长。刚开始时,他们都能耐心接待,并做她的思想工作,但渐渐地便无法忍受。
乡里亦曾派人会同村干部到朱莉叶家里进行调解,但是,朱的丈夫无法接受调解,他说,她就是个神经病,你们也信她的?
乡里建议,如果朱想找丈夫要钱的话,朱可以走法律诉讼渠道,他们告诉她,上访无法解决她的问题。
关键在于,她不仅要丈夫给她钱,而且还要求政府出面解决她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的问题,她要求政府惩罚她丈夫,帮她出气。
所以,乡里的态度让朱莉叶很诧异,也很不满,她认为政府不可能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分明是被她丈夫收买了,不想帮她解决问题。
在乡里僵持不下后,她便开始到县里上访,在县信访局、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县妇联等跑了几圈后,县里找乡里了解情况,乡里如实进行汇报,开始时还为了让县里确信朱莉叶是一个“神经病人”,曾经带着朱的儿子一起到县里接访。
县里也开始逐渐对她“疲惫”了。
朱的丈夫和儿子们,更加忍无可忍,认为朱的作为,让他们在“全县”都颜面扫地。朱的丈夫要求和她离婚。乡里的领导亦建议朱可以与她丈夫离婚。
但朱表示,现在在还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她丈夫都不管她,且在外面还有女人,她如果离婚了,她丈夫就更加彻底不会管她了,也就彻底会跟野花好上了。她认为她不干这种傻事,她说,只要她不和丈夫离婚,她丈夫就得管她,野花也就始终是野花,总有一天会被风吹走的。
在朱看来,县乡两级都“坏”透了,竟然不管她的问题。
她相信,往上走,总有个说理的地方。她相信,共产党一定能帮她出气。
于是,她便开始到市里上访。
从市信访局开始,她走遍了市政府、市教委、市法院、市公安局、市妇联等部门,市教委说她丈夫已经退休了,无法管他的事,她很纳闷,她认为退休了也是教育战线上的退休职工,作为主管单位怎么就管不了呢?其他部门基本上都是批转到县里,县里再批转到乡里。但市妇联的领导亲自到她家察看了情况,并叫来她丈夫调解,尽管问题没有解决,市妇联的领导给她送了100元慰问金和1个水杯。
市妇联的“善举”让她相信自己上访是对的,更加坚定了她往市里跑。
朱莉叶长期往市里上访,让市里很“疲惫”,市里不断批转到县里,让县里“压力”很大,县里不断批转到乡里,让乡里“愁死了”。
在不断上访后,经县法院调解,从2005年开始,朱的丈夫答应每月给她300元生活费。
到2009年时,朱认为丈夫兑现不及时且赖账,于是继续上访追加讨要,并提出要像粮食直补一样直接打在她卡上以留证据。后经县乡调解,朱的丈夫答应标准上浮且打卡,后来,标准上浮到400元每月,但打卡支付的承诺实际没有兑现。
因此,朱继续上访。
伴随着朱莉叶不断臆想着丈夫偷了她的东西,她的诉求亦不断追加。
她现在要求:一是,丈夫给她的生活费要上浮到500元每月且每半年结算一次,要求钱直接打卡;二是,她丈夫躲着不见她,她要求政府帮她把丈夫找回来;三是,要求她丈夫回来后写一个保证书,内容写“凡是朱莉叶家里的东西丢了,都保证是丈夫XXX偷的”,并要求乡村干部在保证书上签字公证。
与此同时,因为频繁臆想失窃,因而频繁报案,派出所不胜其烦,于是才有了本文开篇时与派出所警察老曹冲突的故事。
也因之,从2012年开始,朱莉叶增加了针对江洲乡派出所警察老曹的上访。
五、其他
目前来看,朱的诉求显然是公权力无法解决的。也因之,朱莉叶的上访仍会持续。
朱莉叶的上访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恰恰如此,它才具有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的深度。因此,朱莉叶上访案例本身就具有理解当前农民上访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很难说,朱莉叶的上访不是在维权,尤其是在她上访后期。但我们也分明能够看到,她的上访并非维权那么简单。而当前学界在上访问题研究上却主要且普遍地停留于对维权的想象。
不得不说的是,朱莉叶上访之初并没有任何针对公权力的意图。其初期上访的动力机制实质上是家庭内部纠纷的延伸,其真实含义是求援。如果我们硬要界以一种类型以名之,或许可以叫做求援型上访,其背后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纠纷问题。
然而,针对如何处理朱莉叶求援的事情上,有关各方显然缺乏有效手段,更谈不上解决机制。这种处理人民“小事”的乏力与无方最终在互动中逐步将公权力也绑架进来了。因此,被求援者最终却戏剧性地又有几分必然地成为了求援者的被告对象。
这样吊诡的局面出现其逻辑其实并不吊诡。要想解决这种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还非常艰巨。那就是,在公权力与普罗大众之间应该构建一个清晰的合理的边界。当务之急,也许可以做两件事,其一是,公权力本身需要受教育,它必须明白,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无数个体,它无法做到全知全能,其二是,公民或者说群众同样需要受教育,他们也必须明白,公权力还真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公民或者说群众自己也不是幼稚的小孩,他们自己应该去探索自己日常琐事的解决之道。
当然,朱莉叶因其特殊的“神经病人”的特质,恰好放大了边界不清晰所带来的巨大张力。但也正是因此,其上访故事才显得十分有趣和有意义。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 原标题:刘燕舞、魏程琳:一个乡村“精神病”的上访故事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小婷
-
 “中国打贸易战有秘密武器:AI机器人大军” 评论 14
“中国打贸易战有秘密武器:AI机器人大军” 评论 14 中国不买美国液化气了,换中东 评论 82
中国不买美国液化气了,换中东 评论 82 把中国货“藏”在加拿大,“我们赌特朗普会认怂” 评论 96
把中国货“藏”在加拿大,“我们赌特朗普会认怂” 评论 96 扛不住了?特朗普释放对华缓和信号 评论 461
扛不住了?特朗普释放对华缓和信号 评论 461 和特朗普一起“孤立中国”?欧盟拒绝 评论 62最新闻 Hot
和特朗普一起“孤立中国”?欧盟拒绝 评论 62最新闻 Hot-

中国不买美国液化气了,换中东
-

把中国货“藏”在加拿大,“我们赌特朗普会认怂”
-

涉及稀土,马斯克:正与中方协商
-

美国着急放风“即将与日印达成协议”,其实只是…
-

通用电气CEO:别打了,我们还没给中国交付...
-

哥伦比亚总统: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把我的签证吊销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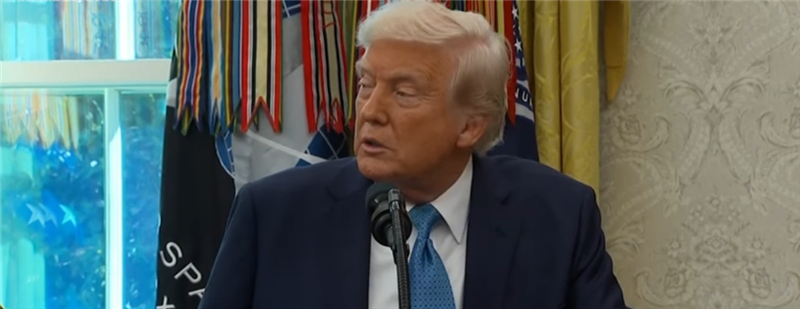
扛不住了?特朗普释放对华缓和信号
-

“孤立中国?东盟不会跟,否则…”
-

“中方对美方鸣枪示警:这回来真的,能一票否决”
-

“特朗普一声令下,美国几十年联越制华努力,白干了”
-

特斯拉净收入锐减71%,马斯克“认怂”
-

普京送给特朗普的肖像画长这样
-

美欧倒逼肯尼亚“转头”,“中国又拿下一局”
-

和特朗普一起“孤立中国”?欧盟拒绝
-

“特朗普把科研领导权让给中国,10年才能恢复过来”
-

鲁比奥要重组美国务院:在大国竞争时代,难以履行使命
-
Copyright © 2014-2024 观察者 All rights reserved。
沪ICP备10213822号-2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220170001
网登网视备(沪)02020000041-1号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沪(2024)0000009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沪)字第03952号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210968 违法及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21-62376571
![]() 沪公网安备 31010502000027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502000027号
![]() 中国互联网举报中心
中国互联网举报中心
 上海市互联网违法与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上海市互联网违法与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观察员
观察员

